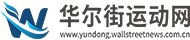【资料图】
【资料图】
作者:周 韫
《源乡》,于季玉而言,算是个界碑。积久的创作,耕耘,一路走来,忽然想回望一下,故乡的岔溪,父母和兄弟姐妹,于是就有了这部书。一部从泥里长出来、混杂着生命原液的心血之作。
季玉的生活积累令人惊叹,不是嗑巴,不是捉襟见肘拽出来的,而是溢出,丰厚得满满当当,源源不绝,如我这般的写作者只有艳羡的份儿了。季玉痛乡亲之痛,痛女人之痛,情感冷峻又炽热。她行走在他们之间,用解剖刀一点一点解析他们的痛之源、之根,扎在血肉深处的陋俗陈规如何去撼动、去改变。
母亲施玉莲身上有着浓厚的旧时代封建妇女的印记,忍受丈夫嫌弃,无休止的出轨,没来由的暴打,连生五个女儿不能传宗接代归咎于自己的肚子不争气。而生了三个儿子的谈艾梅又因为穷,不得不让自己的女儿去为哥哥换亲,这一换直接导致女儿疯了,最后死在猪圈里。她们不同于祥林嫂,也有别于湘女潇潇,她们生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施玉莲为女儿退婚,也会迸发出凤凰涅槃似的亮点,二英经历磨难后顽强地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因为她们正向社会巨变时代巨变走来。但她们仍然无法挣脱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女性的蹂躏戗害。这是要剔除的,要用解剖刀一点一点挖出来的毒瘤。季玉的回溯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警醒意识,这也是季玉创作《源乡》的初衷吧。
“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源乡》有生气,接地气,作者与她所描写的乡野生活水乳交融,活灵活现的细节俯拾即是。有一处写到大英退婚后,男方组织了二三十人的庞大队伍来闹事,把该砸的都砸了,还不解气,又从茅坑里舀了半桶粪水,屋里屋外的泼,甚至泼到灶台上饭锅里。大英躲到亲戚家去了,如果被逮到,弄不好被毁容。父亲呢,在邻居家像个缩头乌龟,大气不敢出,连女人都不如。只有平时软得像面团的母亲施玉莲,被愤怒的人们拽着头发就地拖,手一松,一簇头发落下,“母亲头上又冒出一小块粉皮”“母亲又归位到软面团子”,头上的粉皮和软面团子状态,是母亲的日常,也是贫瘠落后的土地上,女人的宿命。
乡村故事喜闻乐见,讲好乡村故事是季玉创作的现实考量。民间性在这部小说里不是标签,而是与作者血脉相连、贴心贴肺、深入骨髓的痛与爱。曾几何时,作家们关注文本,追逐新奇,传统的故事体被冷落了,不合时宜了。季玉以《源乡》宣示新乡村故事体的回归,以“群像式”的书写,用农民的口吻,农民的立场,为农民立言,这一点与赵树理小说风范相通。同样写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琐碎、新旧观念的冲突;同样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连贯性,首尾相衔,前后照应。所不同的是,赵树理小说继承了宋元话本以及明清小说的传统,采用民间说书式的讲故事方法,而《源乡》虽大体框架相似但在表现手法上进行了更新,以“我”为叙述主体,时而“我”在讲述,时而不知不觉中已经切换视角,嵌入模糊穿插,不着痕迹地完成了时空腾挪,推动故事进展。当然,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旧有秩序的破坏与重建,乡村伦理的交织与悖离,文化层面的审视与冲击,生活方式的改变与多元,等等,所有这些,带着温度与粗粝肌理汇入大时代的风云际会,显示出天翻地覆的样貌。
小说的两个向度是相反的,一方面是剔除,一方面是回归。剔除,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任重道远;回归,则是以新的姿态呈现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样式。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曾有这样的想法,《源乡》如果能够聚焦于一两个主要人物,赋予形而上的意涵,是否效果更好一点,后来否定了这个想法。平涂,群像式,一个个微尘一般的生命个体构成了广阔背景下的芸芸众生,正是作者有意为之。各人头上一方天,脚下一片地。期待季玉有新的作品,新的超越。(周韫)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