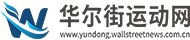无意识的行动
那先于语词世界之发出的上帝盲目的循环运动还尚未是时间性的。它并没有“及时(in time,直译便是没有在时间中发生)”发生,因为时间已经预设了上帝已经从那封闭的精神病的循环中解放出来而自由了。我们通常说的“自时间之始(from the beginning of time)”是要从字面上理解的:正是这起始,这决断/决意的原初行动,构建了时间——将循环运动向永恒的过去“压抑(repression)”创建了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足以容纳线性连续时间的最小距离。我们在此遇到了谢林众多反柏拉图“圈套(stings)”中的第一个:先于语词时间之永恒是无时间的循环运动,是神圣的疯狂,其在时间之下(beneath time),“少于时间(less than time)”。然而,与那些强调谢林与海德格尔对将时间性作为存在的终极的、无法超越的视域的坚称之相似性的人相反,应当道出的是,没有哪处比谢林对于时间和永恒的关系之把握与海德格尔和其对有限性的分析相去更远的了。对于谢林来说,永恒不是时间的一种模态;正是时间本身是永恒的一种特定模式(不如说修饰过程(modification)):谢林至高的努力在于将时间本身从永恒的僵局之中“演绎”出来。绝对者“敞开了时间”,它将循环运动“压抑”进过去,旨在摆脱那在其内心中势要将其拽向疯狂之深渊的对立。另一方面—且,再一次,与海德格尔明显对立—自由对于谢林是“及时永恒”的那一时刻,那无根据决断之点,通过这一决断,一个自由的生物(人类)挣脱、悬置了因果(reasons)的时间性链条,并且可以说是直接与绝对者那超越性的根据(Ungrund,德语,字面意思是非根据)联系起来。这一对时间与永恒谢林式的理解,或者,用更时髦的术语来说,对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理解,因此便是与那惯常的将时间理解为永恒秩序的有限/扭曲反映的观点相反,也是与那现代意义上将永恒理解为时间性的一个特定模式的观点不同:永恒创生了时间以解决它从被牵扯进的僵局。因此,讨论永恒“堕入时间(fall into time)”是及其误导人的且不到位的:那“时间之始”,相反地,是一次胜利的上升,是决断/差异化的行动,通过这一行动绝对者得以解决对立着的驱力之循环运动并从其邪恶的循环中挣脱出来而进入了时间性的延续(succession)。
 【资料图】
【资料图】
谢林在此处的贡献在于一个独特的时间理论,该理论独特在不是形式的而是定性的:与惯常的对时间的理解中将三个时间性维度把握为纯粹形式的之观点(同样的内容也可以说成,通过现在从过去穿越到未来)不同,谢林提供了对于每个维度的一个最小定性。驱力之循环运动内在于其本身就是过去的(in itself past):其并不是曾是现在的而现在是过去的,而是自时间之始过去的。现在便如是是这分开;也就是说,现在代表着那区分的时刻,代表着那驱力无查边的脉搏运动向符号化差异的转变时刻,而未来指定了将至之和解。谢林在此处的批判不仅仅是针对惯常对时间理解的形式主义,恐怕还同样重要地针对了包含在惯常理解中对于现在那未公开的特权——对于谢林,这一特权意味着机械必然性相对于自由的首要性,意味着实在性相对于可能性的首要性。
谢林的“唯物主义”因此是在其不懈坚称中被简要概括的,即我们应当预设一个永恒地过去的时刻,此时上帝自身是任由物质对立(antagonism of matter )的处置的,无法在任何意义上确保A(那光之灵性原则)将最终超越B(那根据之隐晦原则)。由于没有什么是在上帝之外的,这“发疯的上帝”—被压缩的物质之对抗性的循环运动—不得不从其中创生(beget)出一个儿子(Son,圣子),即将解决那无法忍受之张力的语词世界。那驱力之无差异的脉搏运动因此便被诸差异的稳定网络所取代,这一网络维持了差异化的实体的自我同一:在其最基本的维度上,语词是差异化的中介。我们在此遇到了恐怕是对于谢林整个哲学大厦的最基本的概念对立:在那非时间的“封闭的”驱力之循环运动与那“敞开的”时间之线性延续(progression)。通过“原初压抑”的行动,上帝将驱力之循环运动排斥向了永恒的过去而由此“创造了时间”,也即敞开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异,这行动便是上帝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所实施的第一个行动:通过履行这一行动,祂悬置了这一致命的替代选项,即那无主体的自由之深渊与那陷入循环运动的恶性循环中的不自由的主体。
这敞开了时间性维度的“压抑”的原初行动本身是“永恒的”、非时间性的,与那决断的原初行动严格地一致,通过这一行动一个人类选择其永恒的特征。也就是说,就谢林的声称,即人类理智诞生于那将现在-实在的理智从那幽灵般的、阴影般的无意识领域中分隔出来的原初行动,而言,我们必须问一个看上去很幼稚但却至关重要的问题:准确地说,在此到底什么才是无意识?谢林的回答直截了当:“无意识”首先不是被驱逐到永恒过去的驱力之循环运动;反而,“无意识”正是那决定要分裂的行动(Ent-Scheidung),通过这一行动驱力被排斥到过去。或者,用稍不一样的术语来说:真正在人类之中无意识的部分不是意识的直接对立面,那晦暗而混乱的驱力之“非理性”旋涡,而正是意识的创生姿态,即通过其我“得以选择我自己”的决断之行动,亦即,将这个种种驱力整合进我自身的联结统一(unity)。那“无意识”不是惰性驱力的消极填充物(stuff,即前文所译内里之物),注定要被意识着的自我(conscious Ego)之创造性的“人造”活动所利用;“无意识”在其最激进的维度上而应当是我之自我定位的至高行动(highest Deed of my self-positing),或者说,用之后“存在主义者”的术语来说,即是我基本性的“计划”之选择,这一选择为了能够继续运行,便必须被“压抑”,被保持在无意识中,在白日之光之外。此处引用《世界时代》第二手稿那值得钦佩的最后几页:
使得一个人成为真实地他自我那个原初行动先于所有个人行动;但当其被置于欢畅的自由中的那一刻之后,这一行动便沉入无意识之夜中。这并不是可以仅发生一次便停止的行动,这是一个永久的行动,一个无法停止的行动,也因此它也无法被带到意识的台前。要让人知道这一行动,意识自身将不得不回退至无,回退至无束缚的自由中,而便不再是意识了。这一行为发生一次便立刻沉回深不可测的纵深中;而自然也正是因此获得了持存(permanence)。同样地,那意志,起初被定位在起始处而后被引到外部,必须立刻沉入回无意识中。只有以这种方式一个起始方才是有可能的,这起始不再停止作为一个起始存在,因此便是一个真正永恒的起始。在此同样地,起始不能知道它自己这一论断也是真的。那行动一旦完成,它便在完全的永恒中完成了。以某些方式是要真正地起始的决定绝对不能被带回意识;它绝对不能被呼回(called back),因此这将等同于被撤回(taken back)。如果在作决定的过程中,某人保留了其回头检视其选择的权力,那他根本就不会达成一个起始。
当然,我们在此遇到的是那隐秘的中介的逻辑,是差异化之创生姿态(founding gesture)的逻辑;一旦在“非理性”的驱力之旋涡与罗格斯世界就位之后,这一逻辑便必须沉入不可见性。这一从纯粹自由到一个自由主体的转变依赖于存在(being)与成为(becoming)之间的对立,即同一原则和(充足)理由-根据的原则之间的对立。自由包含了同一原则;其指定了那挣脱因果链条的决断之行动的深渊,因为其仅由其自身所根据(当我完成了一个真正自由的行动,我不由任何决定论的理由而做,而仅“因为我想这样做”)。根据指定了作为因果网络而存在着的现实,在其中“无不因一理由-根据发生”。同一与根据的这一对立与那永恒与时间的对立便交叠了:当事物以同一的模式被把握时,他们便显得处于永恒的视角中(sub specie aeternitatis),在其绝对的当代性(contemporaneity,可以理解为共时性)之中,也即,依据其永恒的实质它们存在的那样。当他们以根据的模式被把握时,它们便显得在其时间性的成为中,亦即,作为复杂因果网络的暂时性的时刻,在此网络中过去“根据了(grounds)”现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自由是非时间的:是在时间中一道永恒的闪光。然而,谢林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必然性和自由也是作为非时间性的逻辑和时间性叙事而对立起来的:“同一”也象征着埃里诺学派式的非时间性逻辑性的必然性之宇宙,其中没有自由发展,其中所有事物共同存在与绝对的共时性之中,而实在自由(actual freedom)是仅在时间中才可能的,其作为一实在实体在其成为(becoming)中的一个偶然-自由的决断。此处谢林的努力是将自由设想为同一的非时间性深渊(一个是“其自身的起始”、仅在其自身中被根据的行动之奇迹)且为一个在时间中决断的自由主体之谓项。简单的来说,谢林致力于完成这一从主体到谓项之间的转变,亦即从无人称的“此处有自由”之本我到“祂”(译者注:所有本文中指代上帝的人称代词“he”都为了清晰性翻译为了“祂”,但英文原文都是“he”,即男性人称代词),即一个自由的上帝。这一从主到谓的自由之转变包含了一个严格地与典型的(paradigmatic)黑格尔式的对主谓语的倒置(从“决定性的反映(determining reflection)”到“反射性的决定(reflective determination)”,等等)相一致的倒置:从自由的自我限制/收缩我们穿越到一个自我限制/收缩的(亦即实在地存在的)自由之实体。此处便有了谢林《世界时代》的终极谜题,也是黑格尔式辩证法式倒置的终极谜题:自由“在自身之中”是一个无法被限缩于任一受限实体的无束缚之扩张之移动(movement)——所以它是如何恰好成为一个如此受限实体之谓项的呢?谢林的答案是自由是可以成为一主体之谓项的,但仅在于这一主体已经完成了那自我差异化的行动的意义下,主体通过这一行动其将自身定位为被根据在其被收缩的实质中而同时又不同于它:一个自由的主体必须有一个并非其自身的根据;它首先必须收缩这一根据而后通过那敞开时间的原初决断之行动来假定一个与其之间的自由的距离。
《世界时代》的关键点——与,与此同时,其令人窒息之宏伟的终极手段,谢林思想之绝对整合的符号以及那由于其《世界时代》残篇便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源头文本的特征——就在于谢林试图避开那极恐怖的在纯粹的、极乐的原初自由之无差异与作为自由创世主的上帝之间的中间阶段的那绝望的努力中。在原初自由和作为自由主体的上帝中横插一脚的是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上帝已经是一个主体了(当通过收缩的方式,上帝获取了现实存在(reality)时,祂便是一个主体了),但却还不是一个自由的主体。在这一阶段中,在收缩存在之后,上帝屈从于一个受限循环运动的盲目的必然性,就如一只动物陷入了其自身导致的陷阱而注定要无尽地重复相同无意义的运动。问题是,上帝的理性,其意识到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来得太晚了,比这一盲目的进程晚上一步,于是之后,当祂道出了语词世界并因此获得了实在的自由时,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承认、接受祂“曾收缩”了什么,甚至不是以不乐意的态度,而是在一个盲目地自发性的过程中接受,在此过程中祂的自由意志根本没有参与过。换句话说,问题是,“同一者不得不在神圣生命中承认一个盲目的时刻,甚至说是‘疯狂’的时刻”,而因此创世行为显得是“如果同一者要这么说的话,其是一个在其中上帝要自担风险地参与的进程”。在这三份连续的《世界时代》手稿中,谢林提出了这一自由与存在之间“短路”的创伤性时刻的三种不同的版本,亦即,那打扰了纯粹自由的福佑与和平的,或者用量子力学的术语说,那打破了起源性对称(original symmetry)的原初收缩的三个版本:
在第一手稿中,作为想要着无的意志的原初自由“收缩”存在—即,将其自身凝缩进一个被收缩的物质密度点中—“收缩”那必然性之存在,并不通过一个自由决断的行动:原初收缩不能不发生,因为它从原初自由中以一种绝对直接的、“盲目的”、非反射性的、不可描述的方式生发出来。在此绝对者的第一个内在张力是在扩张性自由与那收缩之盲目必然性之间的张力。
第二手稿,其在自由的方向上走得更远,致力于将原初收缩本身设想为一个自由的行动:一旦原初自由实在化了自身,一旦其转变为一个实在的意志,它便分裂成两个相对立的意志,所以此处的张力是严格内在于自由的:它彰显为在收缩意志与扩张意志之间的张力。
第三手稿已经详细说清了由谢林晚期“实证哲学”所采用的解决方案。其中,谢林通过将整个过程的开始点,那原初自由设想为一个“人造原则”,为一个自由和必然存在的同时性,而避开了自由到存在的转变问题。上帝是一个必然存在的实体;祂的存在是预先被确保的,而正是因为这一理由外在于上帝的世界之创生是一个偶然的、真正自由的行动,亦即,一个也本不能发生的行动——上帝并不牵涉在其内,在其内其本身的存在并不休戚相关。那就前两稿而言的转变、替代在此是显著的:从一个牵涉在创世过程中的上帝,对于这个上帝,此过程是他自己的上架受难(Way of the Cross),我们转变到了一个从一个“元语言(metalanguage)”的安全距离进行创世活动的上帝。
在一个某种程度上有些冒险的理解性的姿态上,我们倾向于坚称,《世界时代》这连续的三稿提供了一个凝缩的、谢林整个哲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的镜像反映(mirror-reflection):
谢林1(其“同一哲学”)是受存在(Being)摆布的(或者说,是鼓吹存在的):即,在其中,必然性围绕着自由,而自由只能居于那“被理解的必然性”之中,在我们对于我们所参与其中的理性必然性的永恒秩序的获悉之中。简单来说,谢林在此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对于他来说对于绝对者的理解包括了其整个内容的绝对共时性、共同在场(copresence);自然地,绝对者便仅能以给予了其永恒内在之充分表达(articulation)的逻辑演绎的模式被设想——时间延续仅仅是我们有限者视角的一个幻想。
与之相反,谢林2(《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与《世界时代》的谢林)是受自由(Freedom)摆布的(或者说,是鼓吹自由的),这也是为什么其核心问题是关于“收缩”的问题:原初自由的深渊是如何收缩存在的?自然地,对于绝对者的表征之模式,逻辑演绎就要让位于神秘叙事(mythical narrative)。
最终,在谢林3中对上帝的理解联结了自由与必然存在,但其代价是哲学向“实证(positive,直译为正向的)哲学”与“否定(negative,直译为负面的)哲学”的分裂:否定哲学提供了上帝与宇宙为何的概念上的必然性的先验演绎;然而,这一“为何性(What-ness,德语为Was-sein)”永远不能解释这一事实,即上帝和宇宙存在(there are God and the universe)。这正是实证哲学的任务,即作用为一种“超验的经验论(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也可译为先验经验主义)”并去“检验”在实在生命中理性构建的真相。
我们倾向于在,一方面,从《世界时代》到谢林晚期的神秘学哲学及其实证与否定哲学的二分法,与,另一方面,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内,从阿多诺与霍克海姆的启蒙辩证法(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到哈贝马斯:在两者中,我们首先有一个浓缩的伟大突破,然而其却最终失败且接下来紧随着一种妥协的构建(formation),一个以极精致的细节详细阐述的庞大系统,但其却因为失去了早期作品的冲劲,而某种程度上显得平淡乏味。晚期谢林解决《世界时代》的困局,是通过在否定与实证哲学的“劳动力分工(division of labor)”中寻求了避难所(否定哲学以一种纯粹理性的方式演绎了绝对者的“诸权力”的系统(scheme),而其实证哲学那一侧则仅仅“确证了(verifies)”这一先验建构在经验性历史内容中的确实性(truth))。在哈贝马斯那里也是一样,其解决了启蒙辩证法的困局,也是通过在“互动(interaction)”与“工作(work)”之间的“劳动力分工”,通过符号学交流与生产性活动之间的分工。简单来说,当《世界时代》致力于直接叙述绝对者的历史,其在一个先验理性系统的最终结果是无保障的,时,晚期神秘学哲学的历史性叙述仅仅是阐释了—可以说是为其提供了血肉—神圣诸权力的先验系统之骷髅,其还是以一种对于最糟糕的那种黑格尔式对经验性内容的理性演绎的无意间的模仿的方式。晚期谢林的问题因此并不是他是一个反动的“非理性主义者(irrationalist)”(惯常死板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斥责),而是他实在太“理性主义”了。当然,这一在谢林和哈贝马斯之间的终极讽刺性是,哈贝马斯,其(在他关于谢林的出色文本《理论和实践(Theorie und Praxis)》中)是第一个清晰阐释了谢林关于《世界时代》的晚期哲学的“压抑性”特征,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中扮演了同样的“压抑性”角色。
关键词: